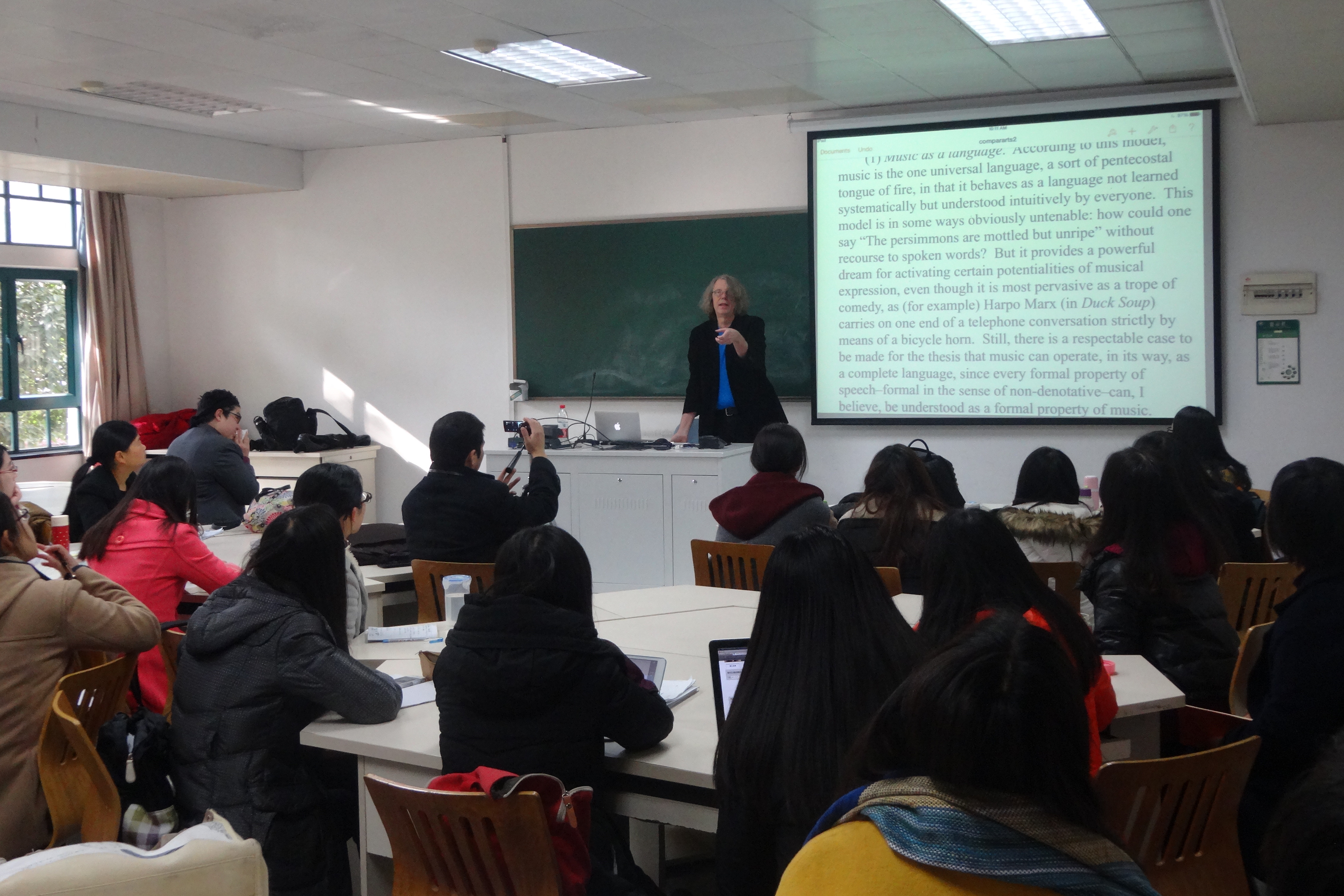2014年12月17日上午,哈佛大学资深教授丹尼尔·奥尔布赖特(Daniel Albright)为我校外语学院的师生们举办了一场主题为《音乐——作为语言与非语言》(Music as a Language and a Non-language)的奇妙的讲座。讲座由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高奋教授主持。
身兼哈佛大学英美文学系教授与音乐系教授的奥尔布赖特提出,我们或许可以不把音乐看作一种形式愉悦的艺术,而把它看作一种语言的艺术;或许可以突破通常所认为的音乐只是一种情绪状态或情境的模糊的移植,而找到一种更为精确的“翻译”方法。虽然就像所有语言一样,音乐也必然有语言覆盖不到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探讨,因为对于音乐,我们有时需要想象力,有时需要辨识力。
奥尔布赖特教授首先引用了贝多芬、舒茨、布里顿、施特劳斯作品中的片断,来说明音乐(器乐)的语言学特征,揭示了音乐与语言之间从最小的语音单位至句法直至整个篇章的“互译”的可能性,并以视听方法向师生们展示了音乐是如何以无言之声描绘英雄、暴君、聪明的或温柔的妻子、布道者、伪君子等生动有趣的人物形象,或如何以音乐独有的“词汇”或“语法”结构,如不同器乐之间的对话等,再现刑场、戏谑、争吵、安抚等戏剧场景,使我们几乎就要听到了音乐在“说”什么。
但是,奥尔布赖特教授接下来警示我们不要陶醉于这种看似轻松的“翻译”方式中,因为我们越仔细审查这一假说,就会越多地发现它的问题。正如将这种再现方式运用到极点的施特劳斯,就连“突然出现的主人公的一根脚趾头都能用纯管弦乐的方式加以描述”,却依然喜欢在音乐中插入一些“扰乱”主题的、含混不明而难以描述的部分,所以我们有必要像探讨音乐——语言“互译”模式一样,了解音乐的非语言学理论和模型,如将音乐视为天堂算术或以声音绘制的星空图的毕达哥拉斯、直至以各种即兴、偶然、不确定的方式进行表演的20世纪音乐家约翰·凯奇,但这并不能使音乐与语言分道扬镳,反倒更彰显出它们的同质性,即语言是一种声音的游戏,音乐也是。虽然音乐并不拥有某种严格的含义或确指,但含义或确指可能就在音乐身边,这里或那里游荡。或者可以用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作为总结,就是音乐不像语言,相反,语言是音乐的一种特殊情形。
接下来,与奥尔布赖特教授同行的玛塔·蒙克洛瓦博士(Marta Monclova)为大家做了一场名为《布莱克·阿尔忒弥斯笔下的贫穷与女性》(Poverty and Women in Black Artemis)的专题讲座。博士通过分析波多黎各作家布莱克·阿尔忒弥斯的小说《看我飞驰而过》(Picture Me Rollin)中女主人公的命运,揭示了美国的贫穷文化,如外表完美、实际繁冗而无效的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底层的女性实际生存发展需要之间的鸿沟。
外国文学研究所
2014年12月28日
(文 向玲玲/ 图胡梦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