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9日,浙江大学外语学院莎士比亚戏剧系列学术沙龙最后一场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外语学院“青芝书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孙柏老师担任主讲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滕威老师担任主持,浙江大学朱振宇老师担任评议及讨论组织者。本次讲座在腾讯会议室举行。

讲座一开始,孙老师指出今天的讲座以《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为资料平台,对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最早的演出——1878至1879年费尔克洛夫和艾尔茜娅·梅、1882年丹尼尔·班德曼剧团、1891年米恩剧团的上海兰心剧院举行的演出一一进行考察。
接下来孙老师主要讲述了1882年丹尼尔·班德曼剧团在兰心剧院的演出。丹尼尔·班德曼是德裔美国演员,1837年生于德国卡塞尔,16岁移民美国,不久成为一名戏剧演员,曾在纽约为德国侨民演出,20多岁时以《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开始他的英语莎剧表演,很快就获得“著名德国悲剧演员”的称号。在美国国内积累了多年的巡演经验后,1879年班德曼率领剧团远渡重洋,赴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新加坡、香港和上海等地进行跨国巡演,一直到1884年初才返回美国旧金山。这次跨国巡演归来后,班德曼出版了一部题为《一位演员之旅,或莎士比亚远行七万里》的游记。在这部游记中,班德曼对每座城市的人地规模、气候景致、风土人情都尽可能地详加记述,特别对于租界地区华洋杂处所形成的独特的社会文化景观多有观察。孙老师认为,这本游记对于早期中西戏剧文化交流的重新认识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上海期间,班德曼认真考察并详细记录了中国戏曲的演出。班德曼认为在起源、性质、风格以及演出方面,中国的演剧是一项特异的体制;然而,对于西方人来说,它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戏剧艺术可言。对于上海茶园台前幕后、观演习俗方面班德曼也给予了详细记述。中国人对于看戏的热情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班德曼注意到,上海戏园的观众席无论包厢还是正厅,座椅前面都摆放有小桌,这种情形“十分接近伦敦音乐厅的形式”。孙老师认为这很重要,因为班德曼很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上海茶园与西方音乐厅的相似之处。在戏剧表演内容上,班德曼发现中国戏曲没有布景,但服装极为考究。同德庇时一样,班德曼强调中国戏曲与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共通之处。孙老师强调,这一认识对于今天的戏剧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西戏剧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比如对于“西剧写实、国剧写意”的刻板印象。但实际上,中西戏剧之间的异同不能被限制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因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基本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到上个世纪30年代初才建立起来。
接着,孙老师发现班德曼对于自己剧团巡回演出的情形着墨不多,但是《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方面的资料。班德曼在上海进行的演出有两套剧目,一套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另外一套是他所拿手的维多利亚时代作家创作的剧目。他在上海演出过程中,上海租界地的报刊舆论给他的评价都是正面积极的,认为班德曼剧团的到来整体提高了上海租界的戏剧表演和戏剧欣赏水平。
随后,孙老师带我们欣赏了班德曼的三部主要莎剧演出,第一部是《哈姆雷特》。1882年5月9日晚9点,莎士比亚的伟大悲剧在上海兰心剧院准时上演。班德曼和他的剧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于班德曼的这场演出,《北华捷报》的整体评价是非常积极的,特别是他独具特色的发音吐字,但是评论者并没有忘记恪尽批评家的职责,即有些地方班德曼通过刻意的发音吐字来营造某种戏剧效果(比如有意把英文字母r读成德语里的大舌音),可惜观众对此并不买账。无论是在英国本土还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大小城市,班德曼的发音问题经常成为评论的焦点,经常引发演员和舆论之间的争论。对此,孙老师认为这与班德曼的德国身份和德国式的表演方法有很大关联。德国人的民族情感和莎士比亚表演的德国学派对班德曼的影响很大,尽管他热爱莎士比亚,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德国学派的莎士比亚表演者和诠释者。
班德曼剧团的第二部莎剧是《威尼斯商人》,具有非常鲜明的种族特色,剧中班德曼饰演犹太人夏洛克一角。孙老师指出,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班德曼不仅是以他所继承的德国学派的表演方法来诠释莎士比亚,而且他是作为一名德国犹太人来演出夏洛克这个复杂的戏剧人物,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对于德国民族文化的认同。
第三部剧是《理查三世》,演出时间为1882年5月20日。这部戏剧存在很多争论,不仅仅是由于表演风格、吐字发音等,更重要的是班德曼用的《理查三世》演出本是18世纪著名演员科利·西伯尔编辑的版本,对于原著的某些部分做了大幅度的压缩,而在另一些地方又有所扩展。《字林西报》批评西伯尔的版本为“拼凑之作”,尽管如此,班德曼的表演仍然得到了最高级别的肯定。
分析完班德曼主要演出的三部莎剧,孙老师指出本次讲座还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我们如何看待班德曼的跨洋巡回演出。孙老师发现近几年西方戏剧学界新的研究方向是全球戏剧史或全球剧场史。20世纪初,丹尼尔·班德曼归田隐居并最终于1905年逝世以后,他的儿子莫里斯·班德曼子承父业,巩固和扩大了巡演剧团在亚洲的业务。按照克里斯托弗·巴尔梅的观点,莫里斯·班德曼沿着“班德曼巡回路线”进行定期的巡演,演出类型覆盖了音乐戏剧、莎士比亚、维多利亚—爱德华时代戏剧、杂耍表演乃至大歌剧,以极富灵活性的剧目选择和表演形态来适应不同地方(特别是殖民地)城市观众的欣赏趣味,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剧场”。孙老师认为这个全球剧场之“父”无疑是丹尼尔·班德曼,他在那个早期全球化的时代所携带和展示的,并不简单是商业性的跨国巡演,而是一幅转变中的世界图景。因为莫里斯·班德曼和他的父亲丹尼尔·班德曼的巡回演出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区别,在丹尼尔·班德曼身上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对于民族文化、民族身份的认同,但是在莫里斯·班德曼身上,这种民族文化的内在张力被大大削弱了。
最后,孙老师强调,全球戏剧运动不仅仅是西方戏剧的全球化,从全球剧场史上来看,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些逆向的运动,比如唐人街里广东移民的粤剧表演。从这些演出里,我们能看到全球戏剧运动不是单方向的,而是一个双向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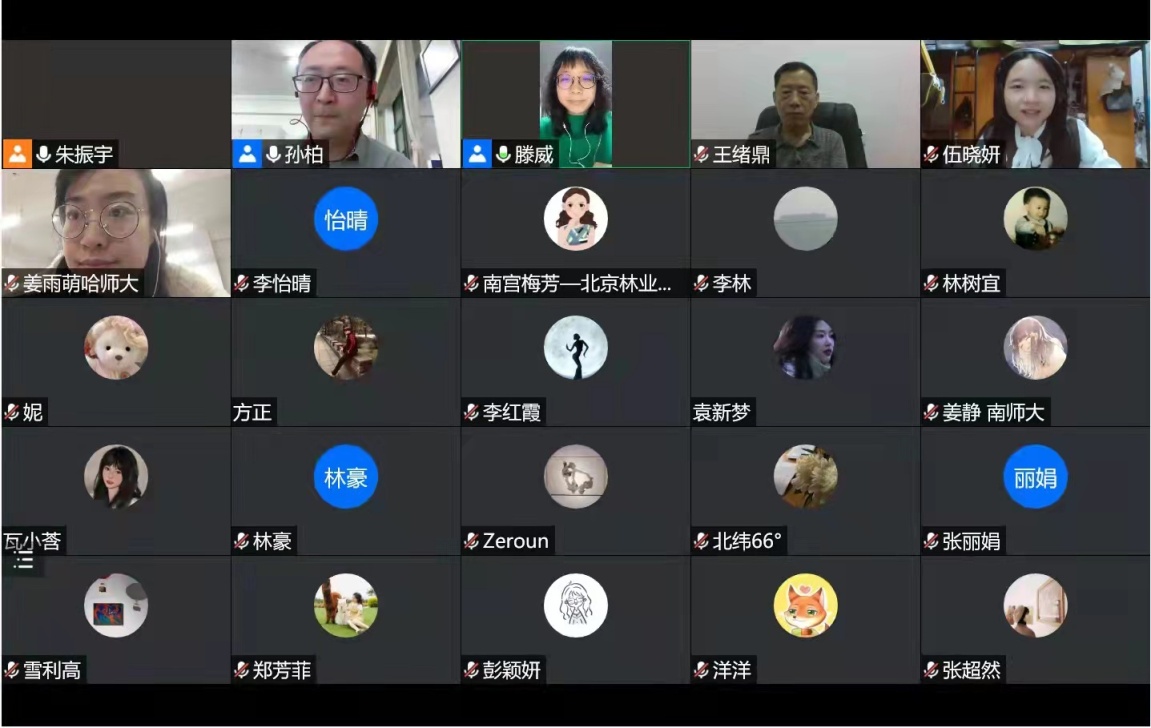
在评议环节,朱振宇老师高度评价了讲座内容的丰富性和深度,朱老师指出,孙老师的研究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不仅对国内莎学研究是一种挑战和批评,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莎学传统以及剧场史的研究也是一种反思和批判。朱老师组织听众与孙老师进行了仔细的学术讨论,本次讲座吸引听众100余人,其中浙江大学听众三分之一左右。

本次讲座由2021年浙江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
(图/文 洪唯)
外语学院 青芝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