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日晚,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系列讲座第五十五讲于线上顺利举行。来自耶鲁大学的国际知名学者卡斯顿(David Scott Kastan)教授与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郝田虎围绕“莎士比亚、弥尔顿与书”这一话题为我们带来了历时两个多小时的精彩学术对话。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高奋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黄必康教授等来自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约一百六十名师生积极参与其中。

讲座中的卡斯顿教授
卡斯顿教授是早期现代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耶鲁大学英文系乔治·M.博德曼荣休教授。自2016年起,卡斯顿教授便担任浙江大学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的首席国际顾问,其多部著作已在中国出版,包括《论颜色》(On Color)、《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after Theory)、《莎士比亚与书》(Shakespeare and the Book)等。此次对话的题目便是郝田虎教授为致敬恩师的经典著作《莎士比亚与书》而取。其中,“书”点明了对话将探索的主题:文学的物质存在。文学从来都只存在于具体的物质形态中,并由其物理载体影响意义的接收与传播。通过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这两位英国文学巨匠的“书”,众人将一同思考图书作为物质载体,如何塑造我们对创造力、作者身份以及世界文学本身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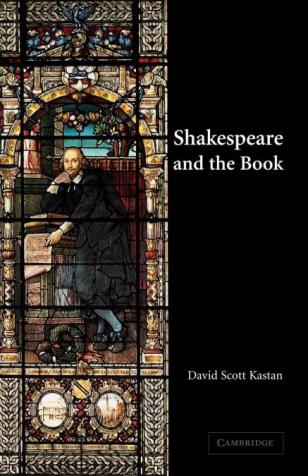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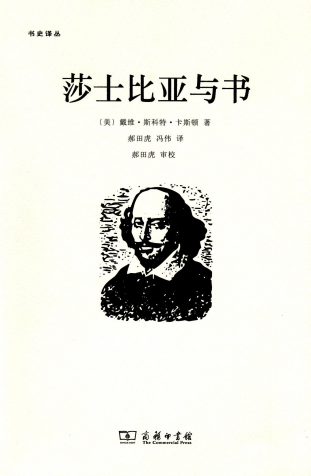
《莎士比亚与书》英文原著(2001)与中文译著(2012)的封面
郝田虎教授率先开启对话。他回忆起约二十五年前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卡斯顿教授有关“莎士比亚与书”的研讨班,深受启发,便想探寻卡斯顿教授如今对该议题是否有新的思考。卡斯顿教授坦言,自《莎士比亚与书》出版之日起,新想法便不断涌现。催生这些新想法的最主要因素是“数字革命”——在当年写作时,数字影印本(digital facsimiles)的可能性与局限性才刚刚显现,书中最后一章对其的预判如今看来虽有偏差,但核心结论依然成立:数字技术能使读者轻松获取大量文本,然而这些文本却更像是一份“档案”(archive)而非某种定本,因为人们仍需梳理这些版本间的复杂关联。卡斯顿教授以自己正在教授的研究生课程为例,说明如今只需十秒就能在网上找到十五至二十五个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1623)的数字影印本,而在二十五年前,这无异于天方夜谭。
那么,为什么说网上的那些数字影印本是份“档案”呢?因为早期现代图书即便出自同一印刷批次,也几乎没有两本完全相同。卡斯顿教授举了两个生动的例子:《暴风雨》结尾费迪南德的台词中,“wise”与“wife”因早期印刷中“长s”的字形与“f”相似,且“f”中的那一小横在印刷过程中易丢失,导致无法确定原文究竟是单纯赞美岳父的睿智,还是也提及了新婚妻子。类似的问题在《奥赛罗》中也有体现。奥赛罗自责时的表述究竟是“base Indian”还是“base Judean”,也因早期印刷中“n”与“u”字形极易混淆、I和J实为一个字母而成为未解之谜。这两个例子鲜明地体现了书籍史并非总能解答文学批评的谜题,反而常常带来更深层的、无法破解的困惑。郝田虎教授对此深表认同,并补充说哈姆雷特那句“To be, or not to be”的著名台词,也面临着不同版本中文本异文(textual variants)所带来的解读迷思。
接着,卡斯顿教授解释了早期现代图书存在复本间差异的原因。当时采用手工印刷,需逐字逐句排版,一次只能印刷单页或单张纸。纸张是出版过程中最昂贵的成本,比人工和油墨都要珍贵。因此,出版商为了尽快盈利,不会丢弃已印刷的未校对页面。在印刷过程中,校对员会边印边校,发现错误后停机修改,导致同一批次的书籍中,既有修改前的页面,也有修改后的页面,组合起来自然各不相同。因此,早期图书常会附带勘误表(errata sheets),用以统一说明这本书里哪些地方存在错误。这与现代读者默认手中的书“完美无缺”截然不同——当我们发现印刷书中的讹误时,会惊讶于这书经过了层层校对,居然还有错误;而早期现代的读者则对此习以为常,自己拿起笔来修改书中的错误即可。


古腾堡与早期手工印刷机
随后,两位教授将话题延伸至“书”的定义,讨论了甲骨文、竹简、卷轴、数字设备等不同物质媒介是否都能被称为“书”。卡斯顿教授提到自己曾计划写一本关于书的书,通过十二个具体案例探讨书籍的历史,书名即叫《书架》(Bookcases)。卡斯顿教授还分享了个人的生活观察:他儿子不爱读实体书,所有阅读都通过手机或电脑完成,因此家里空无一书;而卡斯顿教授自己搬家时,则面临数千册图书难以处置的窘境,即使选择捐赠给学校或卖给二手书店也并非易事。卡斯顿教授承认,电子书的确为阅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图书馆也逐渐倾向于收藏数字版本以节省空间、方便更多读者使用,但实体书所承载的情感联结——比如祖母留下的带有批注的藏书,或是作者题赠的关联版本(association copy)——是电子书无法替代的。同时,他还担心文字的数字化会让写作过程中的修订痕迹丢失,因为现在的作者常常直接以最新的版本覆盖草稿,未来的学者可能无法像研究数字时代之前的作家那样,通过手稿来探究使用电脑写作的当代作家的创作过程。郝田虎教授对此则持相对乐观的态度,认为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出类似“数字考古学”(digital archaeology)之类的研究门类也未尝不可能,到时候文学研究者要考察的对象可能不再是某位作家的手稿,而是他/她的硬盘了。
郝田虎教授转而询问莎士比亚后续对开本的情况,包括1632年的第二对开本、1663/64年的第三对开本以及1685年的第四对开本。卡斯顿教授解释,后续对开本并未因再版而更接近莎士比亚原作,反而因重印新增了错误。而莎士比亚之所以能成为英国文学甚至英国性的象征,也并非全依仗莎翁本身的“天才”或者所谓的“永恒与普世价值”,其中也有英国政治殖民事业的扩张等因素。以此为契机,卡斯顿教授讲述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一段趣闻:博德利图书馆创始人托马斯·博德利(Thomas Bodley, 1545-1613)最初认为早期现代英国戏剧是“无用的闲书”,因此不愿收藏这类有伤风化的“通俗读物”。直到1624年,第一对开本才进入著名的牛津大学图书馆。1663年第三对开本出版,并在1664年的第二印本中新增了七部据称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实际仅一部属实),图书馆便将第一对开本当作“多余的”书卖掉,换成了“更完整的”第三对开本。1905年,有人带着一本家族珍藏的第一对开本前来修复,图书管理员立马认出了它——那正是当年博德利图书馆卖掉的第一对开本,上面还留着牛津大学的皮革装订和印章!随后,博德利图书馆通过公众募捐以当时创纪录的三千英镑价格购回此书,让它又回到了曾经的家园。

郝田虎教授与卡斯顿教授进行学术对话
两位教授还讨论了莎士比亚对开本读者的问题。郝田虎教授指出,手稿证据表明,17世纪手稿札记书《缪斯的花园》的编纂者约翰·埃文斯(John Evans)阅读的是第一对开本,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William Sancroft)阅读的是第三对开本。而我们的另一个主角弥尔顿亲笔批注了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2019年的这一伟大发现开启了我们对英国文学“双子星”文学关系的新一轮热烈探讨。弥尔顿应邀为第二对开本题词,于1630年写下了向前辈莎士比亚致敬的著名诗篇。如果说早期现代图书像卡斯顿教授所言,是“不完美的书”,那么,形形色色的读者,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完成了书的使命,使不完美成为完美。正如拉丁语谚语所称,书籍的命运有赖于读者的能力(Pro captu lectoris habent sua fata libelli)。我们认为,弥尔顿是莎士比亚的完美读者和完成者。那么,弥尔顿的完美读者和完成者又在哪里呢?
对话结束后,进入观众互动环节。高奋教授首先提问,考虑到莎士比亚作品的编辑、印刷和出版历史,文学作品的物质载体是以哪些方式对“作者意图”(authorial intention)这一概念构成挑战的?卡斯顿教授回应,莎士比亚写作剧本是为了舞台表演,而非出版书籍,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他的“作者意图”至关重要。剧本会因演员临场发挥、服装道具调整、印刷排版错误等诸多因素被修改,所以所谓的“作者意图”并非一个单一的存在,而是分散在剧场、印刷铺等多个环节中,涉及演员、印刷工、出版商等多方的劳动,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参与者在作品塑造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高奋教授询问有关“作者意图”的问题
接着,黄必康教授分享了自己对伦敦书籍出版中心迁移的观察,询问此中心从威斯敏斯特向东迁至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缘由。卡斯顿教授表示,这一迁移是书籍民主化和识字率逐渐提升的体现:早期卡克斯顿的印刷业服务于贵族和学者,书籍版式巨大、价格昂贵,不易随身携带;随着识字率逐渐提高,尤其是英文圣经的出版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学习阅读的热情,书本变得更小巧、廉价,出版中心也迁移到更易接近的区域,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图书,白话英语(vernacular English)也随之变得重要起来。

黄必康教授提问有关伦敦书籍出版中心迁移的问题
接下来,在场的研究生们也踊跃参与到了讨论之中,就“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封面肖像与本·琼森短诗的互文关系”、“斯宾塞与莎士比亚进入印刷市场的不同方式”等议题与卡斯顿教授和郝田虎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
讲座最后,高奋教授总结道,这场对话围绕莎士比亚作品的“物质生命”展开,从纸张页面到历史上的各种印刷体系,再到数字屏幕,让大家认识到书籍的物理形态并非只是文字的容器,更是文学创作、传播和跨时空跨文化转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不仅存在于文字中,更存在于印刷、阅读、传播和持续的重新解读中。高奋教授代表浙江大学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以及所有观众,向两位教授的精彩分享致以诚挚感谢,同时感谢黄必康教授的热情参与,也感谢每一位在线听讲的观众。这场充满启发性的学术对话在温馨的致谢中落下帷幕。
文/舒好,图/左珈源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供稿



